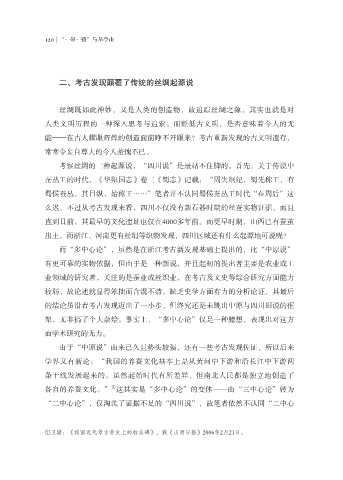Page 126 - 内文
P. 126
120 “一带一路”与皋亭山
二、考古发现颠覆了传统的丝绸起源说
丝绸既如此神妙,又是人类的创造物,故追踪丝绸之源,其实也就是对
人类文明历程的一种深入思考与追索。而贬低古文明,是否意味着今人的无
能——在古人耀眼辉煌的创造面前睁不开眼来?考古重新发现的古文明遗存,
常常令妄自尊大的今人羞愧不已。
考察丝绸的三种起源说,“四川说”是最站不住脚的。首先,关于传说中
蚕丛王的时代,《华阳国志》卷三《蜀志》记载:“周失纲纪,蜀先称王,有
蜀侯蚕丛,其目纵,始称王……”笔者并不认同蜀侯蚕丛王时代“在周后”这
么迟,不过从考古发现来看,四川不仅没有新石器时期的丝蚕实物证据,而且
直到目前,其最早的文化遗址也仅在4000多年前。而更早时期,山西已有蚕茧
出土,而浙江、河南更有丝绢等织物发现,四川区域还有什么起源地可说呢?
而“多中心论”,虽然是在浙江考古新发现基础上提出的,比“中原说”
有更可靠的实物依据,但由于是一种新说,并且起初的提出者主要是农业或工
业领域的研究者,关注的是蚕业或丝织业,在考古及文史等综合研究方面能力
较弱,故论述就显得笨拙而含混不清,缺乏史学方面有力的分析论证,其最后
的结论虽沿着考古发现迈出了一小步,但终究还是未跳出中原与四川旧说的框
架,无非搞了个大杂烩。事实上,“多中心论”仅是一种臆想,表现出对这方
面学术研究的无力。
由于“中原说”由来已久且势头较强,还有一些考古发现佐证,所以后来
学界又有新论:“我国的养蚕文化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和沿长江中下游两
条干线发展起来的。虽然起始时代有所差异,但南北人民都是独立地创造了
ꨁ
各自的养蚕文化。” 这其实是“多中心论”的变体——由“三中心论”转为
“二中心论”,仅淘汰了证据不足的“四川说”,故笔者依然不认同“二中心
ꨁ卫斯:《我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标志碑》,载《山西日报》2006年2月21日。